【白夜谈】白粥的小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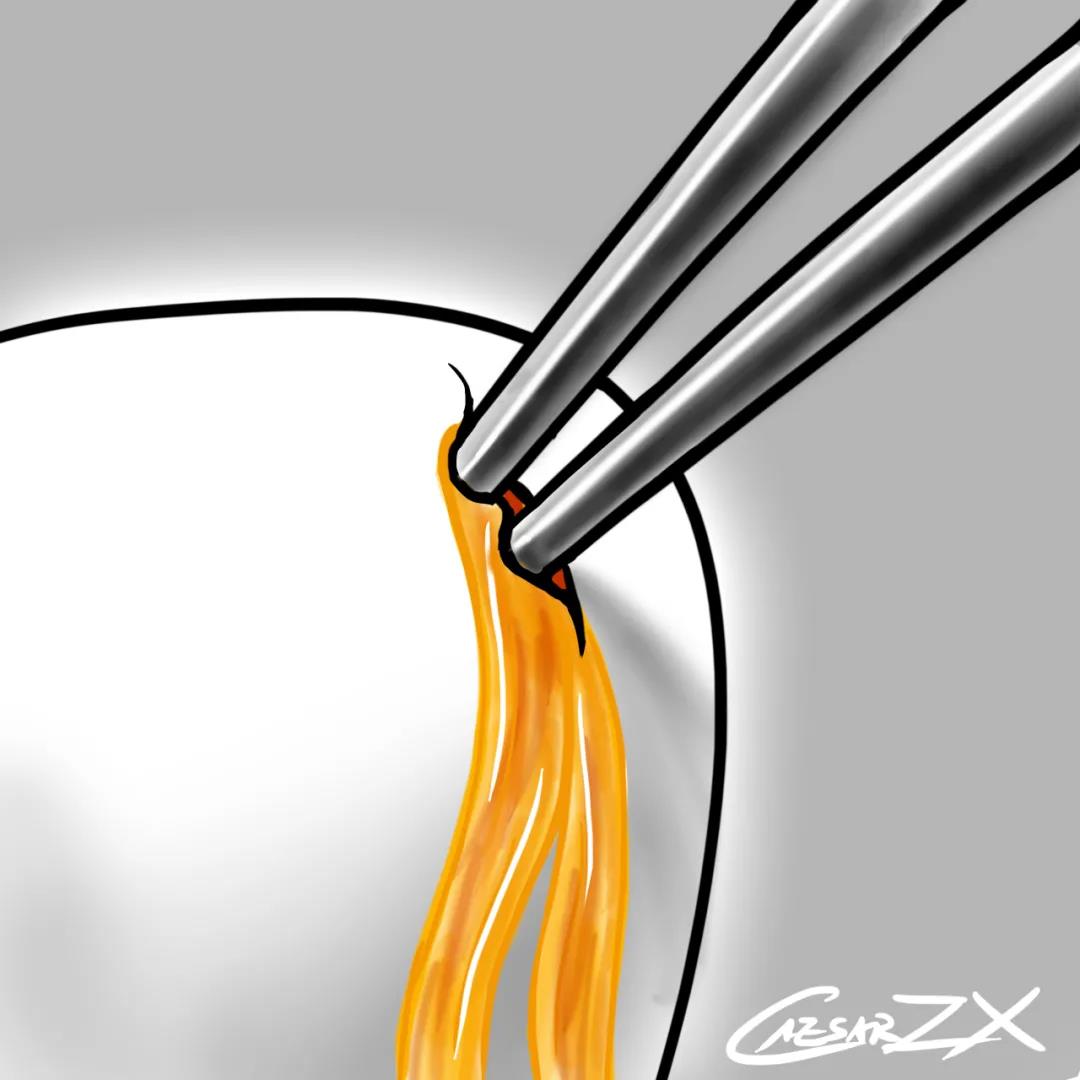
我算不上是吃货,甚至应该算是对食物兴趣不足,身为烹饪爱好者的先生经常击节哀叹我吃不出美食的好坏,我倒也不太在意,毕竟我感兴趣并且在意其好坏的事物太多了,也不少口腹之欲这一条。但是,唯独对于白粥,我却有种莫名其妙的穷讲究。每次吃粥我一定要搞出三四样小菜,一个个小碟子铺了一桌子,配着热气腾腾的粥,毫无意外又温暖服帖的味道;这样吃完一餐,一天都会精神倍增,大概也算是一种专属于我的“仪式”了吧。
说到小菜,首先要提的就是油鸡枞。我有位最好的朋友,会每年给我寄她家里自己炸的鸡枞,简陋的塑料罐子,层层叠叠用胶带封着,鸡枞满塞到一开盖子就溢出来。第一次吃到鸡枞时我感动的简直快哭了,那种香气难以描述,所有被它琥珀色香油沾染到的饭食都骤然上了两个档次。因为实在是太好吃,那一天的公司年礼我也选了网上买的油鸡枞,还专门在附言里写着,“新的一年,送您点好吃的”。

后来,朋友送的这两瓶迅速被我吃光了,我就也去网上买了年礼用的油鸡枞。这回送来的鸡枞罐子要漂亮很多,标签上还画着鸡枞拟人吉祥物,给人非常不祥的预感……果然,一口下去我就楞了。这东西又硬、又淡、又糙,像是在嚼树枝或者茶叶梗;看看原料表,香菇占了大头,估计鸡枞只有那么几根,在拼命发挥它们天生的充沛香气盘活后进的香菇。那一刻我深深感到了对接到年礼的合作伙伴们的愧意,如果您读到了这篇杂文,请一定记得那玩意儿不是我心目中的鸡枞,我也知道那不好吃啊,我不是故意硌您牙,您听我解释!
怀着巨大的被欺骗的屈辱,还有早饭没有鸡枞可以吃的恐慌,我又去网上买了三四瓶不同的鸡枞来试毒。有号称农家手工的,也有号称年销几百万瓶的;我刻意避开了所有打着“馈赠佳品”SLOGAN的商品页面,也小心翼翼地屏蔽掉了“买二送四”之类的超值优惠;但最后买到的,无一例外,依旧是非常糟糕的鸡枞。有些可能稍微接近我印象中的味道,另一些更接近我印象中的茶叶梗,总之,它们都无法让我的白粥仪式效力翻倍,它们让我有些沮丧。

于是,我终于还是磨磨蹭蹭一步一扭地去找朋友讨鸡枞了。几句话过去,善解人意的她就提出要家里把去年没消耗完的再分我一些,我心里又踏实,又特别不好意思。朋友还解释,外面卖的鸡枞之所以又硬又糙,主要是因为两点;要么是原材料里杂菌远多于鸡枞,要么就是炸的方式不对。
第一点很好理解,真正的鸡枞菌只有在夏天的雨后才会冒出头来,而且还没法养殖,要靠赶山的人们亲手一根根采集,再运到早间的集市上贩卖;这样金贵的东西,当然一瓶里放的越少越好咯,反正炸出来都是棕褐色一根一根的,肉眼确实看不太出来。第二点也是出于成本考虑,要想把鸡枞炸出最好的状态,就得用热油从头炸到尾,大概需要炸一整天;这样做出来的鸡枞内里是酥脆的,香气都被锁在油里,即好入口,又好吃。而大部分小作坊等不起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又不想耗费那么多的油,他们就索性把鸡枞丢在大锅里先煮熟,然后再炸。
朋友说每年一到了鸡枞的季节,她家乡大街上就弥漫着煮鸡枞的绝妙香味;鸡枞的香气留在了汤水里,而汤水又会被作坊的人毫不怜惜地当街倒掉;一条街是香的,香到让人想要不顾体面地讨来汤水回去喝,但这条街出产的鸡枞却也永远地把灵魂留在了街上。
鸡枞之外,还有一样小菜是季节性供应的,那就是我先生老家腌制的风干鸡腿。这东西是我第一次跟着他回扬州老家时吃到的,外表平平无奇,就是一根白煮鸡腿,手撕成一条条的肉丝。说实话,回他家那段时间在吃上我是相当不适应的,总感觉每家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都有点软绵绵的,都偏甜。但那一口鸡腿下去,我之前的所有不满都被一把掀翻。这种风干鸡腿首先是很咸,咸中拌有鸡油的鲜香,好像所有的脂肪都在风干过程中与盐分融为了一体,完美均衡地渗入每一丝肌理之中。另外,鸡肉本身意外地多汁,像是煮汤的鸡捞出来微微晾干一样,毫无“腌制品”刻板印象里的柴口。每一条下去,舌头先是品到咸,然后品到鲜,再品到肉香,就差不多得赶紧再拿下一条了。

可能在饭桌上我吃的确实是过于显眼了吧,临走的时候我先生的亲戚硬是塞了三四个大鸡腿让我带回北京,我假意推脱了一下下——不敢推的太久万一他们真不给了呢——赶紧抱着鸡腿就跳上了返京的火车。回家以后,先生替我把鸡腿煮好撕好,冬天里它甚至没必要放冰箱,就放橱柜里,早上取几条来就白粥。猫对这鸡腿有着异样的兴趣,常常长久地蹲在橱柜下守候,但我自己吃尚且不够呢,它至今是没有这个口福的。
后来我拐弯抹角地又去催先生替我讨鸡腿,但他说这种鸡腿不是时时都有,它的制作颇要几分天时地利。那位亲戚自己开了个茶楼,也附带厨房方便肚饿的牌友们吃完面条;于是每年秋天结束的时候,厨娘就买来肥硕的鸡腿,剖开抹盐和香料,然后挂在房檐上开始风干,大概到过年时节正好能吃。

但这风干期间天气既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冷则味道渗透的不够均衡,热则容易腐烂;空气的湿度也要够,并且不能下雨下雪——反正是一大堆的条件凑在一起,颇有些妙玉存无根水的意思。那次我捧走的三四根就是人家整个茶楼一年仅存的储备了,到了第二年,为了定向爆破我这个馋鬼,亲戚家专门弄了20根肥鸡腿,挂在房檐上叮叮当当很是壮观,方圆五里的野猫都闻讯赶来围观。遗憾的是那一年的鸡腿可能是彼此之间间距太近了一些,有些地方风干的不够“熟”,不够咸,味道略逊了一点点。而在我殷切的期盼中,眼看着又到了要吃这一口的时候,我正与野猫一同盼着今年的鸡腿早日熟成。
其他的小菜相对来说就好入手的多了,包括宝塔菜、小黄瓜、姜片在内的各色腌菜,还有王致和的腐乳,以及逛超市时随手拿的日式渍物。稍微值得提一嘴的可能是咸鸭蛋吧,这东西就像是盲盒,直到你打开一个蛋为止,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抽到一顿什么样的早餐。有时候敲开大头用筷子稍微一戳——北京这边的习惯是把咸鸭蛋一剖为二,南方的习惯似乎是用筷子掏——就会见到橘黄色的亮油涌出来,这一刻,无论你早上刷牙是不是牙龈又出血了也无论窗外是不是又下雨了穿不了刚买的新鞋;你心里一定是快乐的,一定是叹了一口气,而后嘴角微微一动的。
我至今依旧怀念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菜市场买菜,那边有个个子高大的鲜族阿姨,提一篮咸鹅蛋在卖。每一个都比鸭蛋贵几毛钱,但比鸭蛋大,而且切开之后油足的简直过分,让人想要刮下刀刃上的油舔干净。腌鹅蛋的质地也更为沙绵一些,不那么咸,配着北方特别咸的咸菜一起,再来碗剩饭煮成的白粥……
这样想想,我对白粥的情结可能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吧,不是什么高级吃食,却是实打实“家”的味道。而现在,在一个忙碌的周一上午,我早早起来做完昨天写好的稿子的修订工作,然后放任琐思飘飞,信笔写到这里;落笔这行字时正好听到电饭煲滴滴答答地叫了起来,昨晚定时煮上的粥好了。侧头想想,冰箱里小菜的储备还够。
今天也是个好日子。